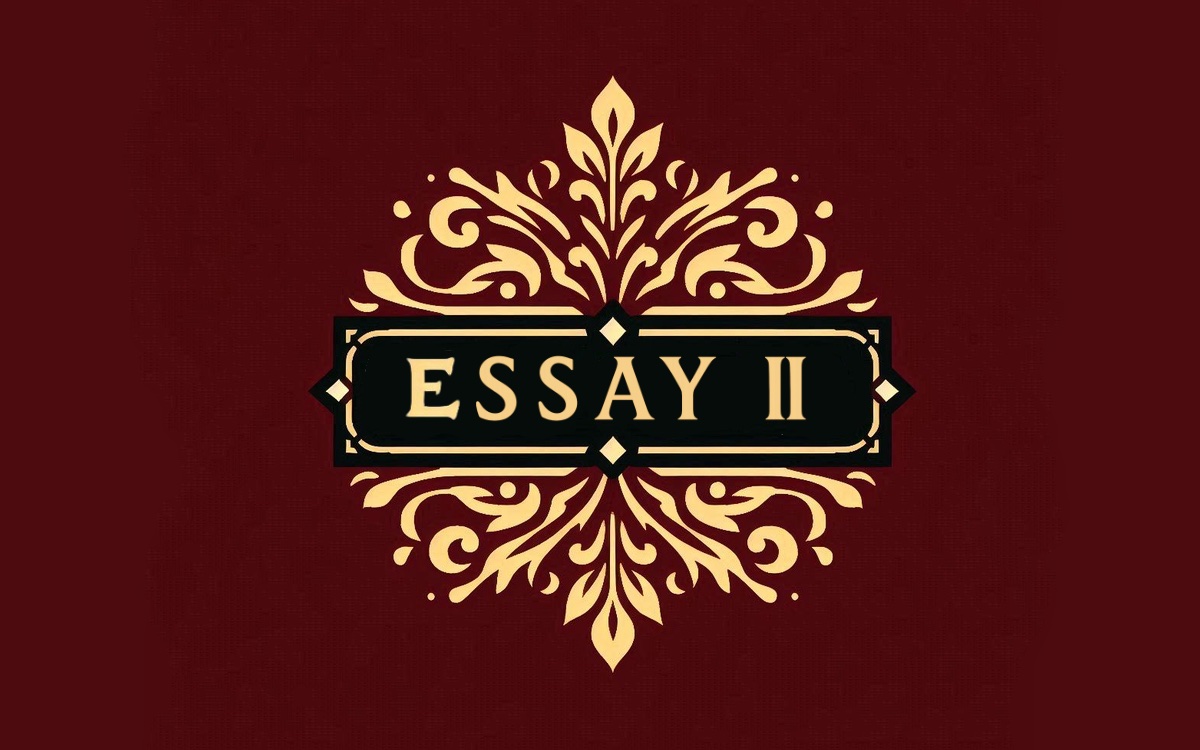可是,被邀请的人一个也没有来。因为恰恰是那些与这件事关系最密切的人几乎没有注意到孩子们的游行。——《时间窃贼和一个小女孩的不可思议的故事》
相当一部分任务管理工具和方法论,即便不是充满善意的,最少也有工具价值。然而在流传之中,多数工具都遭到扭曲,成为了商业意识形态的载体。四象限(豪威尔矩阵,Eisenhower Matrix)和看板(kanban)等均为适例。
诚如《娱乐至死》作者波兹曼所言,工具从来都不是中立的,它有其适合的使用者,但任务管理软件开发商和生产力网红试图让每个人都参与模拟跨国企业高管的任务游戏。这种身份和工具的彻底分离,这种对现实世界的拒斥,是所有任务管理悖论的根本原因。
四象限
艾森豪威尔总统——就是组织诺曼地登陆的那位,之后被选为总统——将其这一思想工具发扬光大,但是到了各路开发商和生产力网红手里,四象限却变得面目全非。
管见以为,四象限根本不是一项常规任务管理工具,至少,你既然有空读这篇文章,恕我直言,它大概率不是为你设计的。详言之,这是一款为顶级精英设计的工具,对于普通人而言,其意义仅仅在于让使用者认清现状,这本身无可非议(甚至很有价值),但厂商玩的把戏是,让任何人都来玩盟军最高指挥官、美国总统或科技公司巨头的角色扮演游戏。
四象限试图将任务分类,并提供相应的处理优先级。简言之,四象限以是否紧急和是否重要两条坐标轴,将待办事项大致划分为重要且紧急、重要但不紧急、不重要但紧急以及既不重要也不紧急四个象限。重点来了:
- 重要且紧急之事,马上完成;
- 重要但不紧急之事,稍后安排;
- 不重要但紧急之事,甩给别人(这是最重要的);
- 既不重要也不紧急之事,弃如敝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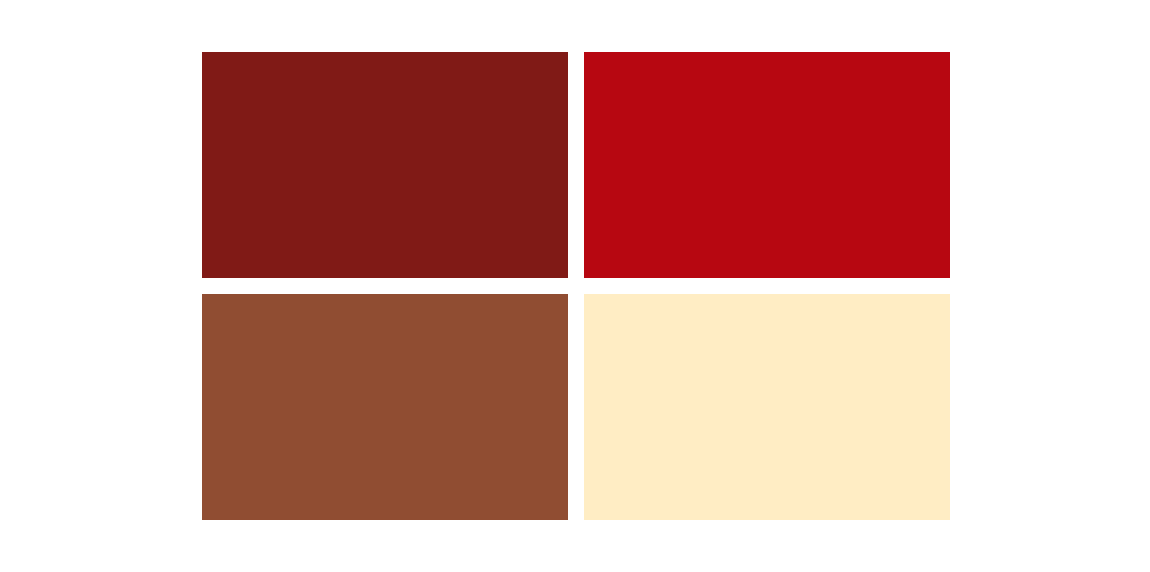
在 Stephen Covey 那本再版无数的《高效能人士的7个习惯》中,四象限被推到近乎任务管理原则的地位,但它的隐含假设是:你可以把肥差留给自己,脏活委托给别人。在后续发展中,四象限的最高峰恐怕是 Timothy Ferriss 的《每周工作4小时》,如书名所言,作者自己完全只做最重要的工作,整个世界都则成了他的受托人,处理任何你能想到的垃圾任务。
和你预想的,大多数人并没有那些高管、政治家或头部网红的余裕,我们通常都忙于紧急事项,其中不少还是紧急但不重要之事。它们是从哪里来的?上游的不重要但紧急之事。我很少有机会和昔日法学院的同学碰面聚餐,因为各人要么在和政府部门拉锯(律师)、要么处理当事人的投诉(法官)、要么写一些自己都不信的论文(大学老师),这些任务,大部分来自上游。玩笑是真实且残酷的:所谓的重要,就是对自己重要;所谓的紧急,就是对别人重要。
问题就在这里:多数人没有选择的权利,至少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都无法改变任务的分布状况。易言之,在根本上,四象限不是一个容器,而更像是一面镜子,照出你的真实任务环境,甚至反映你的社会地位。这绝对不是开发商鼓吹的那种容器,可以轻松填满或取出东西。
Stephen Covey 的机场成功学名著开门见山,用词是“高效能”而非“高效率”。细细品味之下,就能发现其中令人毛骨悚然的差异:任何人都可以高效率,包括古代的奴隶、近现代的煤炭矿工或者缅甸的电信诈骗犯罪分子,但是谁有资格高效能?当属地位较高的知识分子,尤其是白人男性精英。Covey 所谓的重要事项,是身心健康、事业、家庭,并且比如有一个或复数个孩子,这些都是白人精英男性的标准配置。但我猜测 Covey 的读者可能有九成以上还挣扎在温饱线附近。
Covey 旨在解放精英的生产力,这背后是一条一脉相承的线路,从科学管理大师 Taylor、家政运动先知 Catherine Beecher 到如今鼓吹科技精英统治论的 Elon Musk。精英当然有权利左右任务分布,只要他们乐意,既可以把所有资源都投入到对人类没有任何好处尽管也没有什么坏处的棒球卡片收集活动上,也完全可以投身于物理学前沿并留名青石(比如公子哥德布罗意)。
精英没有问题——我本人就很钦佩德布罗意,他完全可以只成为半个薛定谔,即分流的那一半,但他决定严肃投身物理学——问题是有人让你假扮精英(或者,如果您已经有所成就,那就假装更上流的阶层)。精英游戏,就是主流任务管理的核心。
诚然,如果有人只是初遇四象限,旋即野人献曝,建议将其当作电脑壁纸,据此划分待处理的文件,那无可厚非。但那些基于四象限开发的软件则大有问题,毕竟,它们不可能坚守照妖镜的角色,不可能嘲讽用户(在统计学上,绝大多数用户的处境必然不佳),唯一出路就是吹捧和恭维用户,即便用户无事可做,也能想办法用一堆貌似重要的事项填充收件箱,游戏化之路由此打开。
收件箱是本作下一篇的主题。一言以蔽之,把四象限当作容器的方法和工具都走错了方向,只要工作环境没有变化,社会地位没变动,任务分布基本也就巍然不动。如果你每天围绕着别人甩过来的破事儿晕头转向,那么多一只任务管理的乌鸦在耳边报丧似乎也没有什么意义。如果你有幸每天专注于自己的事业,那么也没有必要专门养一只任务管理软件当作报喜鸟。
这就像记账,如果你只是不断记录,然后每个月看看自己浪费了多少钱,感叹一下,接着浪费,一切如故,那么即便拨烂了算盘子,也意义了了。
四象限真正的价值在于反映现实,这种事,在一段时间里做一次就够了,接下来是要想方设法从根本上改变任务分布,尽可能专注于重要事项,而非瞎忙或穷忙。虽说四象限理论上可以提供持续的任务管理,但其核心方法是委托,这已经排除了绝大多数人持续使用四象限的可能性。
某种程度上,几乎所有任务管理理论都是四象限失效的产物。
看板
四象限的难兄难弟为数不少。另一款被扭曲的知名任务管理工具是看板(kanban)。
看板最早被用在汽车生产领域,由丰田公司在上世纪开发,并开启了所谓的精益生产时代。鉴于现在已经没有不精益的企业了(如果有的话,马上会死),有必要简述从大规模生产到精益生产的转向:众所周知,福特汽车以其流水线布局开启了现代生产,但正如技术史专家大卫·奈所言,福特属于大规模生产,忽视现实世界的复杂性——这一点很重要,和任务管理软件行业遥相呼应——在生产上,综合通用零件、单一机器和流水线等物质技术,以至于几乎任何人都可以充当工人,而不需要多少培训;在供应上,把供应商当作虎视眈眈的狼群,通过投标大浪淘沙,而不愿意与之沟通;在消费上,从最早的几个车型到后来只生产T型车,无视消费者反馈。
丰田的精益生产则不然,当时,“人无我有”的时代已经过去,福特以及其他欧美厂商较少的车型已经无法满足消费者。考虑到早在流水线问世之前,车企已经陆续挥别手工制作而进入通用标准件时代,似乎组装出更多型号并非难事。但问题是:你怎么知道消费者喜欢什么?毕竟,车也和电影一样,多的是叫好不叫座的型号。
答案是看板。看板不能保证消费者照单全收(除非在福特、微信和 OpenAI 那种垄断时代),它更像是有策略的试错法,关键在于检验环节,产品必须通过市场验收才算走完一生,否则生产再多也是徒劳。易言之,丰田公司重视的不是各个车间交付出去多少东西,而是这些交付出去的东西是否得到市场认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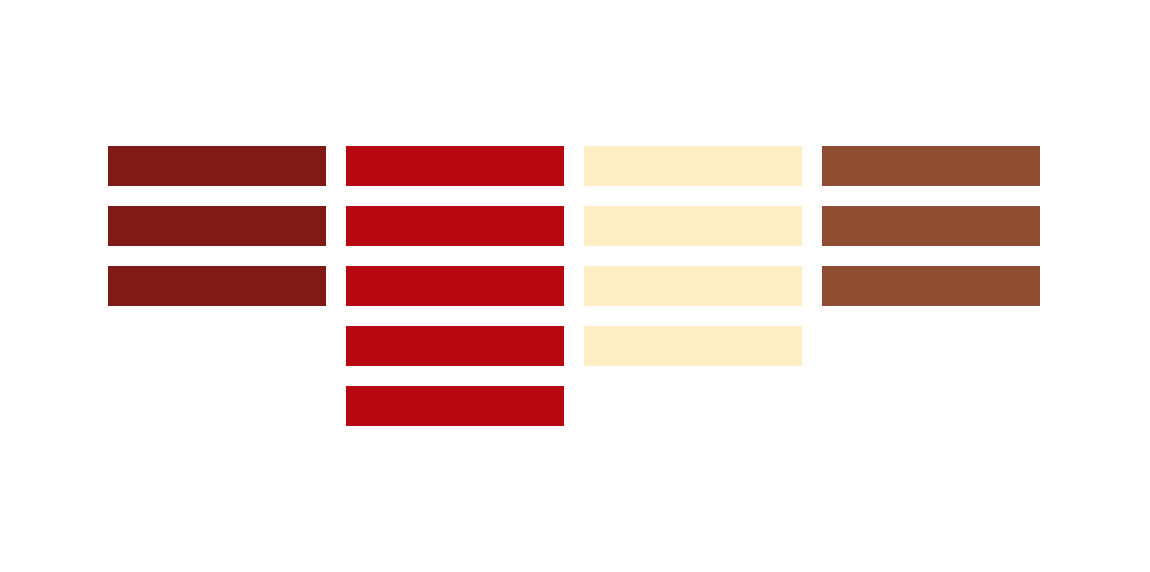
看板也被任务管理圈子误解了。多数看板软件,旨在让你填满各个环节,似乎自己像个成功的CEO那样,手里握有无数工作。这完全不现实。很大程度上,看板工具也是在勾勒你的任务环境:除非你自己经营一家企业,或者负责一个独立的项目,否则你根本用不到看板,因为你根本没有参与整个生产流程,只是其中的一颗小螺丝钉。这也就不奇怪,那些自嘲自己在排泄物上雕花的家伙,也可以大大方方使用看板——反正没有真正的、直接的、血腥的市场检验。
看板在个人任务管理中的局限,是 Taylor 管理革命的遗产之一:上班是为了挣钱,不是直接做出好产品,生产好产品的是企业。错的不是看板,而是滥用看板的推手。
小结
多数开发商和生产力网红的错误(或诡计),就在于将分析性工具本体化为某种可能的、而且相对是理想的结果,然后以此为前提设计种种任务管理工作流。
在绝大多数人都不是 Bill Gates 或 Elon Musk 的现实中,任务管理主流却怂恿用户照搬精英的任务管理方式,并且这些方法论通常还是开发商或者生产力网红自己的意淫。批评与事者非蠢即坏,一点也不冤枉。
分析工具本体化已经大错特错,而在接下来的执行环节中,多数工具又滑向了游戏化,这是任务管理产业的第二宗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