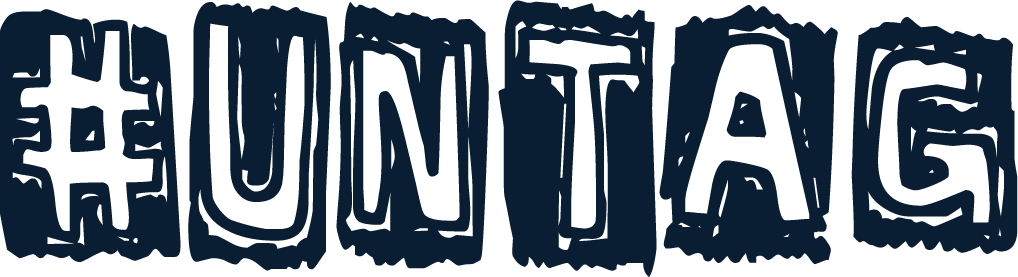对于这两条路径——扩张性的禁欲主义和内包性的享乐主义——的真正本质,我们也说不出什么所以然来。一个文明可以任选其中一条:向宇宙进军或者切断与宇宙的联系。——斯坦尼斯瓦夫·莱姆:《其主之声》
我们从未拥有如此繁多的工具。知乎文章侧边和微信公众号推文中间,满是软件及其使用手册的广告;往前回溯几十年,《全球概览》给新社区主义者提供建设的工具清单,从农耕器械到个人计算机;上世纪初,垂直文件柜广告将效率工具与摩天大楼等量齐观,塑造了办公工具的高大形象……每一个时代的消费者都是一群布里丹毛驴,不知道该选用哪一款工具。
而每个年代都有一群人——我们姑且自认为是其中一员——似乎受到某种禁欲主义的桎梏。比起花枝招展的印象笔记,我们宁愿在朴素的 Markdown 编辑器里敲敲打打;即便 Apple 已经在两个 macOS 的大版本中更新了 Live Text,Geek 们还是对开源的第三方 OCR 识别引擎情有独钟。而开源、低技术和通用技术之于我们这些家伙,就像红外线保健和磁石水晶理疗之于太空时代的长辈们一样,令人趋之若鹜以至于无可救药。
这背后应拥有某种选择的逻辑。稍微了解个人电脑发展历史之士,恐怕会指责我们为前朝遗老,而实际上我们经历的不过是互联网浪潮的余波,而非那场真正的惊涛骇浪,于是前述评价很快降低为食古不化或崇洋媚外。
但毕竟,在那些我们乐意与之亲近的工具,和我们敬而远之的工具之间应当存在某一条界限,这条界限是如此模糊,以至于只有眯着眼睛的时候才若隐若现,一旦试图伸手触摸,它却像艾舍尔版画中的蝙蝠和鸟兽一样,霎那间化作碎片而散。
当我试着站得更远一些,从远处所见的那条朦胧界限,其实是延伸型工具与娱乐型工具的分野。
工具,从压迫、解放到娱乐
在20世纪下半叶之前,关于工具性质的讨论似乎并没有太大意义,盖所有的工具都是条条大路通罗马,从核子实验室中中走向普罗大众,从压迫的工具成为民主的工具。杰克·古迪在考察书写时,就指出它既是压迫的工具,又是解放的工具;在核冬天威胁下如履薄冰的维那,意识到控制论暂时是统治的工具,未来则会成为民主化的工具,令社会成为一个自我稳定的系统;在进化论已经统治世界的当下来看,这种工具性质的变迁没有任何怪异之处,因为在某个环境中用途鲜明的一个器官,完全可能在其他环境中被挪作他用。技术和工具的进化也正是如此,以至于到了麦克卢汉,“媒介即讯息”和“地球村”的口号已经名正言顺。
但工具却没有这样线性发展。我们确实没有迎来1984广告中的冰冷世界,但我们发现生活走向了另一个令人不愉快的极端:娱乐至死。人们从前想要一把更趁手的锤子,但现在却关心其手柄上的雕刻花纹;人们原本想要一辆更大马力的汽车,现在却在追逐更个性的喷漆效果;最初人们要求性能更好的电脑,但现在却往机箱里面塞满灯泡和衣不遮体的美少女手办;虚拟现实(VR)最成功的应用恐怕是恋爱游戏,当然由于政策因素,卖得最好的还是虚拟对砍游戏。关于技术的发展,或许还是科幻小说家莱姆的预见最为深刻:技术让我们迎来一场性爆发,随后又是集体的性无能;在那之后,我们又将对其他领域产生近乎于色情的冲动。
把玩工具本身,成了最终的目的。
在某个时间段之前,打磨工具和玩物丧志——尽管并不总是有害——的区别无法体现。在读中学之际,由于学业繁忙或电子设备受到管控,两类人或许难以区分。可一旦有了充裕的时间,能够随意购买想要的电子产品,很快我们就会发现:一类人流连于开箱测评视频,紧追最新潮的手机和电脑,或者每年换一款任务管理软件;而另外一类人则关心怎样利用好这些工具,拍出更好的照片,或者写出更流畅的文章。工具会选择他的受众,苹果手机成为街机,iMac电脑统治了白领写字楼,这些现象掩盖了工具对受众的选择作用,我们只有细心观察一个人使用快捷键的手势、一个人对字体的配置方案、或者他有没有改过默认Dock设置,才能看出他是哪类人。
延伸型的工具让人勇往直前,而娱乐型的工具虽然也讨喜,偶尔也能解决眼下问题,却容易让人原地踏步——或者用现在最流行的说法:内卷。
工具的本质:媒介即讯息
When he said “the medium is the message”, he meant that you have to become the medium if you use it.——Alan Kay, User Interface, a Personal View, 1989
当麦克卢汉高喊“媒介即讯息”时,他获得了整个世界的回应,并且多是积极的声音。麦氏尤其受到中国人民的欢迎,盖彼时的中国与前几次工业革命均擦肩而过,但根据麦氏的说法,只要能够采用新媒介(主要是互联网),后来者也能迎头赶上。紧跟着麦克卢汉,托马斯·弗里曼的《世界是平的》也被译作汉语,成为鼓舞人心的精神燃料。
不过,并没有多少人理解麦氏的观点。那些自称人人都是产品经理的家伙,只是在用麦克卢汉的名义抛售新奇设备以及公众号排版课程,而这些商品要么即将变成电子垃圾,要么马上被下一代产品拍死在沙滩上。他们说的媒介,不过是销售的媒介;他们的口中的工具,不过是商业的工具。
问题的根源在于,对“媒介即讯息”的诠释往往建立在笛卡尔剧场模型之上,顺着管道隐喻,将人视为一个端坐剧场之中的灵魂,通过各种媒介——窗户、大屏幕、望远镜或潜望镜——去观察世界。这种将观察者和被观察的世界分隔开的模型,基于灵魂全能的假设,意即只要有合适的媒介,灵魂就能从世界中源源不断地获取信息。吾辈不以为然。设想一个全能的灵魂,不仅引入一个额外实体,更因为这个实体全能而等于无能,既然它可以解释一切,那它实际上就不能解释任何东西,就像一个拉着自己头发希望将自己提起来的莽汉一样。鼓吹媒介万能,和批评媒介是形式主义或新瓶旧酒一样只是在隔靴搔痒。
相较笛卡尔模型下的诠释,Alan Kay 的理解更为美妙。他所说的内化工具,其实颠倒一下句子结构,就是“工具是身体的延伸”之含义,这才是从芒福德到麦克卢汉一脉相承的媒介理念。我们创造并使用工具,不是因为这种工具为我们提供了什么,而是它让我们行至更远;而一旦从字面意思上理解麦克卢汉的格言,结局就是我们止步于追求媒介本身,陷入娱乐至死:赛璐珞金箔钢笔,每一颗键帽都嵌有微雕的键盘,塞着泳装手办的组装电脑机箱……
至此,那条像银河一样真实却无法触摸的边界终于水落石出。我们喜爱的工具,是那些可以不断拓展边界的工具,即延伸型工具;而令我产生生物性防御情绪的,则是那些拓展可能性阙如的工具,即娱乐型工具。
当 Jobs 设计第一代麦金塔电脑时,他想带给世人的是“大脑的自行车”。您会用自行车做什么?去镇上买菜,环岛观光,或者绕着古都奈良瞧上一圈。自行车是带你去另一个地方——通常不远——的工具,是腿脚的延伸;而个人电脑,则把你带到线上社区。我有一辆海啸自行车和一台苹果电脑,但我讨厌室内自行车架和金屋藏娇的电脑机箱(有手办的那种),盖前一类工具让人足迹延及天际,而后一类却把人困在原地。
工具的塑造:能力层级系统
The important thing to appreciate here is that a direct new innovation in one particular capability can have far-reaching effects throughout the rest of your capability hierarchy. A change can propagate up through the capability hierarchy; higher-order capabilities that can utilize the initially changed capability can now reorganize to take special advantage of this change and of the intermediate higher-capability changes.——Doug Engelbart, Augmenting Human Intellect, 1962
延伸型的工具之所以是延伸型的工具,有赖于一个让其发挥能力的层级系统之存在。
中世纪的玻璃制造技术已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那些意大利的工匠已经把玻璃器皿做得比宝石更加华丽,足以令埃及艳后脖颈上的珠宝黯淡无光。然而,在天文学乃至整个科学界产生从纯粹逻辑到实验观察的范式转变之前,玻璃仍然仅仅是玻璃,只能成为器皿或者装饰品,而无法成为天文望远镜上最重要的部件。黑色火药在中世纪的资产阶级手中,可以用于推翻封建主义,但是在同时代的中国却只能用来逗弄神仙妖怪。20世纪之前的差分机甚至无法被建造,只能在威廉吉布森的科幻作品中统治世界。
文化和地域差异同样构成系统环境。法国人把 Opniel 折刀称作自己的第十一根手指,因为这把碳钢木柄小刀和法国人的饮食习惯严丝合缝:切面包,片熏肉,处置水果。而惯用筷子的亚洲人,则很难把小刀视作义肢——相反,他们有筷子。
第一代控制论科学家维纳将宇宙视为信息系统,并认为它有望自我稳定,这给冷战那一代的知识分子以精神支柱;而在核子危机的阴云淡去之后,美国智力增强研究中心的一个小伙子开始思考更多,他幻想着一种增进人类智能的工具:相比控制论科学家的抽象表述,此君将人体看作一个层级结构,认为小变动固然只能直接影响周围环境,但在一个层级系统中,变化能够不断向上传递,最终引发系统的质变。他做了一个简单的思想实验,即设想最初的笔如果重如砖石,则整个书写文化恐怕都会和今天迥异——事实上,这个实验根本不用做,因为世界各地的书写方式已经提供了现成的对比素材,而古罗马对莎草纸的依赖,更是被历史学家视作帝国倒塌的积木块之一,盖罗马在失去埃及地区之后便盛极而衰——埃及恰恰是莎草纸的产地。
至于那个埋头苦思的年轻人,他沿着自己对层级系统的思索,最终发明了鼠标,而“恩格尔巴特”的名字也流于青史。
鼠标显然是延伸型工具,因为它在人手和屏幕之间建立起一道跨越山谷的大桥,进而让人能够控制贝塞尔曲线或三维模型;触摸屏同样是延伸型工具,它在对精度要求稍低的场合甚至比鼠标更好;但目前的虚拟现实和增强显示则不好说,除了打个响指让扫地机器人开始干活,它们的延伸能力还远远不足——至于使唤智能机器人,更古老的声控技术估计更适合,好像也轮不到元宇宙。能力型的工具能够组成高楼大厦,而娱乐型的工具虽然也不错,但往往只相当于雕梁画栋。
总之,我们有了一个识别延伸型工具的策略,而非仅凭开源、跨平台或界面复古与否胡猜。一个身处层级系统,并且能与之交互的工具,很可能就是延伸型工具。使用交互界面最时尚的工具,一点也不意味着用户是技术弄潮儿,相反,很可能是被开发商牵着鼻子走。现在我们知道,为何那些关于笔记软件、写作软件以及任务管理工具的讨论最后都会变成鸡同鸭讲的争吵,只因为人们很少会抬起头观察一下,周围是否有一个系统存在。
玩具和工具:不同跨度下的视角
雕塑家的槌棒是浑圆的,这可以让它在手中不断地旋转。首饰匠的镂刻锤是一种非常精致的工具,用来在金属上做慢工细活。当勘探者凿石头的时候,他的鹤嘴锄恰好与人的臂摆相平衡。——维克多·帕帕奈克:《为真实的世界设计》
苟以延伸与娱乐将工具简单二分,则难免出现看似无法解释的矛盾。例如 Shortcuts 和 LaunchBar,一个是图形化自动化工具,另一个则完全依靠脚本,两者却都被批评为玩具——前者是编程者门外汉的亵物,后者则是代码魔术师们的智力体操。
事实上,只要调整时间跨度,看得比一臂之遥更远一点,则两者都可以划入延伸型工具。批评 Shortcuts 的人往往着眼于其功能数量,但忘了 Power User 们也许只是想在排队时更快地掏出二维码,便人利己;而批评的自动化脚本的家伙则以软件工程师为背书,以为脚本比成品软件低级,殊不知自动化玩家只想让机器帮忙排好文章或泡好咖啡,早点下班、多陪家人,并非总要成为下一个比尔盖茨。
固然,工具的使用完全在于用户,不乏一些如同现代玻璃工匠的 Shortcuts 玩家,他们热衷于制作一些长达数百步的 Shortcut 动作,然后一次系统小版本更新就令其构造物轰然倒塌,随着我们就可以在 Twitter 上看到“苹果要完”的声讨(你们知道我在说哪个意大利人)。但总体上,自动化工具的延伸属性还是强于娱乐性。
时间跨度本身也会影响工具的属性。在环中国旅行时,我的同伴背着十块钱的地摊货背包,这简直要气死张口“背负系统”闭口“人体工学”的职业背包客。实际上,此君旅途大多在飞机和火车上,比起背包,更多时候是与拉杆箱为伴;而其旅行又正值夏季,即便是最昂贵的户外背包,在身上不出五分钟也会湿透。苟钻研论坛许久,背着最新款的限量版 Arcteryx 滑雪背包坐飞机,岂不贻笑大方。
此外,同样是延伸型工具,在不同时间跨度下也各有千秋。排斥封闭工具是一种政治正确,比如 Microsoft Office 就让人敬谢不敏。我个人曾经非常讨厌 PDF Scanner(PDF Expert 出品的一款扫描工具),它弃原生框架不用,导致我在 AirDrop 时总要打开二级菜单,延伸能力极差。但如果拉长时间线,考虑几百上千页的文件(这在职场中司空见惯),则这个乌克兰特产的单张扫描速度优势便累积起来;一旦将长达几个小时,甚至一两个通宵的扫描工作视作一个整体,则专用软件就能脱颖而出——在不同的跨度下,我们有理由眯起眼睛看待工具,可以在大尺度下忽略细节上的拓展性。
- 订阅 RSS,第一时间收到文章更新:https://utgd.net/feed
- 加入 Slack 群,直接和主笔交流:https://utgd.net/member-community
- 成为会员,享受更多增值服务:https://utgd.net/memb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