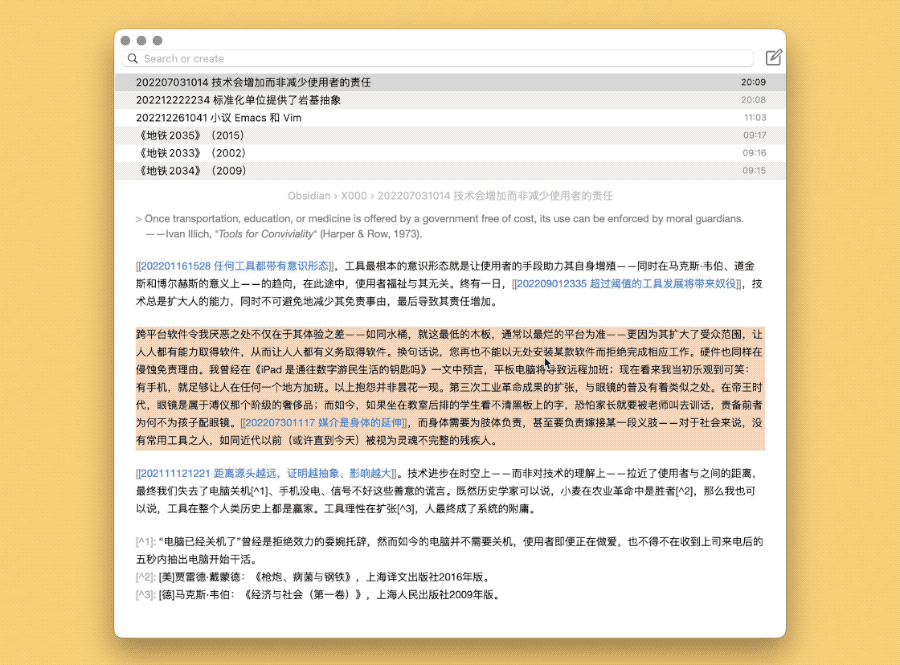卡片笔记常被吹捧为拼贴的技术,即每次只写一小块儿,待有读者上钩时,再拼凑出连篇累牍的文章,这种作者,仿佛是专卖预制菜的小吃店老板,早已准备好一大锅半成品,客人进店后,把配角蔬菜汆个水就能上桌。甚至有人为 Obsidian 开发了拼接文章的插件,可以把双向链接替换成其指向的笔记正文,从而把一堆支离破碎的笔记变成又臭又长且不明觉厉的“文章”。
我对拼接文章的说法不以为然,在《卡片笔记与高产:从采集式到农耕式写作》中,我也批评了那些将卡片笔记作为万能金克拉肥料的论调。毕竟,你不能通过堆积排泄物得到农场。卡片笔记不是拼接的技术,相反,它是扦插的艺术。
从形式上看,很容易误会卡片笔记只是机械拆分:几千字的文章,沿着小标题几刀下去,剪成十几篇百来字的碎片,然后美名其曰原子化笔记。但真正的拆分操作,其实更近乎于园艺中的扦插:待一段话瓜熟蒂落,方才将其剪下来,精心修剪,并细心培育成一篇新笔记,令其自成一套完整的上下文,既与母株藕断丝连,又自成语境。
概言之,笔记并不是机械的排版技术,而是考验品味的园艺艺术。
扦插案例一:读书笔记
传统笔记,往往从头到尾一气呵成,需要作者精于谋篇布局,而卡片笔记的兴起,这是传统笔记方法遭到质疑后的产物,试图让写作变得轻松。
然而,我们在卡片隐喻的道路上似乎又走得太远,催生出了所谓大纲式写作,比如在 Roam Research 中,写一句话换一行,一篇原本可以行云流水的文章,往往也被梳理成大纲,这简直就像用解剖刀和药剂匙品尝美食。这已经不是原子化的笔记,而是进入了量子尺度,根本让人捉摸不透。如果卡片笔记仅仅是尺度上的转换,那未免过于简单。原子化之功,固然包括降低写作压力,但更在于舍一蹴而就、从循序渐进,令数字花园踏实生长。
处理读书笔记,尤其是现有的长篇笔记,乃扦插的特长。在接触卡片笔记之前,我们可能已经攒了不少笔记,虽有冒犯,但这些笔记一般都是流水帐,除了让人回忆往昔,似乎也没有其他用途。卡片笔记的初衷,就是令其中多的观点独立成篇,以便径直引用,而不用重新翻阅整篇读书笔记。施以扦插之法,可将传统读书笔记转为卡片笔记。
以《论剽窃》一书为例,阅读时,我在各章下均留有笔记,只是详略有别;而其中思考较深的部分,就可以拆出来,作为新笔记;同时,在原始文本被剪下之处留一个双向链接,指向新笔记。读第一遍时,可能感受较浅,只写了三五篇新笔记,但也无妨,书本来就需要多读几遍。重读之时新的摘抄和笔记,仍然可以先补充到旧读书笔记,洎乎思考成熟,方移入新文档,并同样留下双链,以示出处。如此读书,如同栽培植物,源源不断。
具体到扦插笔记的技术细节,则视各人所用的笔记软件而定。Roam Research 和 Obsidian 用户均可在插件市场中搜索,比如后者,就有一个拆分笔记的插件。我乐意与前述工具为友,但相当讨厌和任何工具结盟,因此我自己编写了自动化脚本,举凡支持纯文本格式(包括 txt、md 和 markdown)的编辑器均可用之,例如上一代卡片笔记工具 nvAlt 及其精神继承者 FSNotes。我编写的自动化工具,可以将当前笔记中选中的部分复制下来,转移到一则新笔记中,从而完成扦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