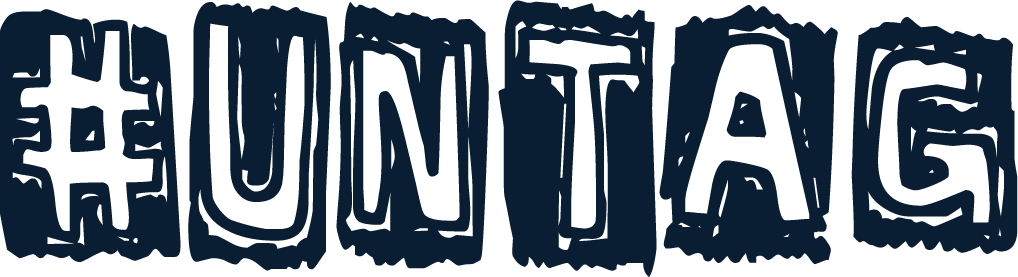动物可以划分为:a.属皇帝所有,b.进行防腐处理,c.驯顺的,d.乳猪,e.鳗螺,f.传说中的,g.流浪狗,h.包括在目前分类中的,i.发疯似的烦躁不安的,j.数不清的,k.浑身绘有十分精致的骆驼毛,l.等等,m.刚刚打破水罐的,n.远看像苍蝇的。——博尔赫斯
在描述一个对象时,司马贺(Herbert Simon)指出了一种精致的对称:你可以描述一个对象的性质,例如圆的几何特征;同样,你也可以描述如何得到该对象,例如如何绘制一个圆。在高中以及之前的教育中,世界似乎可以被还原为这种对称的表达。
惜乎,只要对象稍稍增多,精妙的平衡便随之瓦解。考虑最大众的隐喻:三体问题,仅仅增加一个对象,恐怕就无法再用简单的方程组来描述这组物体。
何况是数量以成百上千计的笔记。原本已经让人头痛不已的动力学问题,很快上升成一种宇宙学论题。面对如此难以言说之物,古代的地图测绘方法再次登台,我们尝试摸索笔记的结构、模式、层级,自上而下,假设笔记应当有一种应然的结构。然而,一波又一波的笔记方法论本身就意味着地图进路存在问题,或许我们应当考察相反的方向,自下而上,尝试在每一篇笔记中穷追不舍。
自上而下:地图隐喻
在所有具体方法论之前,有一个常常被忽略的大前提:我们总是假设自己的笔记——至少在理想中——有某种相对可控或至少可以辨识的地形地貌,而这种认识又会影响后续的写作。
人类的以简驭繁的历史与其自身的历史一样悠久。在特定历史时期内,简化地图确实行之有效。古代流传下来的地图大多高度扭曲,将如今看来的弹丸之地拉伸到地图的四个边角,而实际上占了地球表面绝大部分的海洋以及未知大陆则当作零星的小点,或者干脆视而不见。这种扭曲有现实意义,毕竟绝大多数古代探险家和旅行者不太可能前往世界边缘。其中一张中世纪末期的朝圣地图 Tabula Peutingeriana^1,可算是这类主观方便主义地图的代表作,它展示了一条朝圣之路,沿途的重要地点被画在一条康庄大道上。尽管朝圣之路非常曲折坎坷,根本不是条直线,但这不妨碍朝圣者使用地图。正如我们熟悉的地铁线路图,其对应的真实轨道并非线路图上那漂亮的几何形状,只是对于潜入地底的人而言,曲线没有意义。

在当代,除了地铁线路图,几乎所有的平面地图也都保留了人为扭曲和节略^2,在现实中面积不小的极北岛屿和南极大陆硬生生被压成了小土块。对于世界上绝大多数人来说,这无伤大雅,毕竟除了极光观光旅游,多数人恐怕一生都不会想到要前往两极地区。
在笔记的抽象世界中,我们也继承了地图绘制员的任务,用扭曲、简化但有用的印象取代真实。但和中世纪的朝圣者或者地铁乘客不同,笔记作者面临着一个快速变化的世界:笔记世界不仅是一个被感知到的世界,同时也是一个被快速塑造的空间,结果我们的笔记往往变成了模式所预测的样子,但这个模式,很可能是别人的心思,无论善意、愚蠢还是邪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