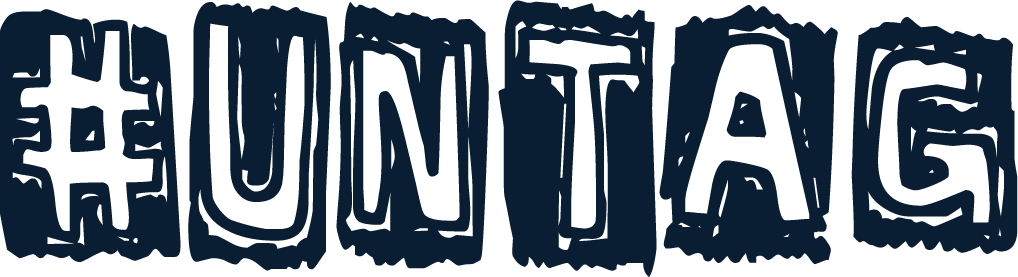做事严肃的人,无论从事科学工作还是艺术创作,常常会把文献和资料摆得到处都是。乔布斯虽然以极简主义闻名,但与其只有一盏台灯的公寓截然相反,乔的工作室中倒是资料汗牛充栋。
在摆弄资料方面,很少有人能够超越艺术家大卫·霍克尼。他是画家出生,却凭一己之力几乎把艺术史中的神话掀了个底朝天:文艺复兴时期突然涌向的一大批人肉照相机式巨匠,几乎都是对着投影描摹图像,而不是抄起一根画笔和一把铲刀就向壁虚构。
霍克尼依靠的工具非常简单:一台打印机。一旦他打印并平铺了艺术史上最重要的作品,事情就一目了然:大部分逼真的作品,几乎都有不同程度的畸变,就像你自拍时画面边缘那些不自然的部分。这意味着名匠们必然普遍采用了透镜,否则不可能所有人都犯了一样的错误。绘画中的透视畸变,是文艺复兴版本的人工智能文生图六根手指 bug。
打印机实属佳例,让人直观感受到媒介的颠覆性力量。从文艺复兴到霍克尼这五百多年间,尸体足够环绕博洛尼亚大学好几圈的学者难道都是瞎子,看不到夸张的畸变吗?^1他们恐怕只是没有条件把大量复制品摆在一起、铺开观察。^2
乔布斯的工作室,霍克尼的打印机,再到侦探的调查墙、杰克伦敦挂在洗手池上方的词汇卡片、流言终结者堪比军火库的工作间、设计师田中一光直接贴在窗玻璃上的素材胶片……种种把素材摊开的媒介,总有惊人的力量。
较之前述种种媒介,电子屏幕似乎更加可及,画布软件也无处不在。但事实并非如此。问题在于,平铺本身不是目的,而是手段,关键在于平铺之后你又做了什么:怎样观察,如何重新分组、排序,以及你打算把资料晾上多久。除非我需要制作电子文档(例如画一个案件当事人关系图,分享给团队中的其他律师),或者长期马不停蹄四处奔波(例如连续打飞的出差),否则平铺工作更适合在物理空间中继续,而不必首先向昂贵的智能设备寻租。
结果,在保留画板软件的同时,我又回到了霍克尼的打印机方案,只不过不是传统机型,而是便携式热敏打印机,纸张尺寸也仅仅是信用卡或名片大小。这些小巧并且可以像便利贴一样移动的标签纸,连同墙面一起,把整个公寓变成了一台大型低技术计算机,承载了不少时间跨度较长的项目,从布置家居(我先后尝试了好几种媒介,每一种都很有收获)、琢磨设计稿、对比大件商品到还原案件事实。

多数交互总是文字优先,而图像是第二公民……